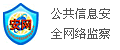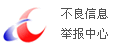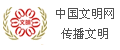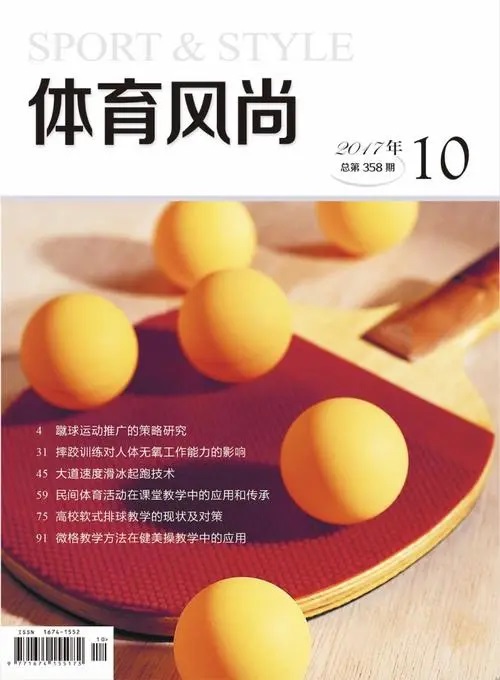
主管单位:深圳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
主办单位:深圳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
出版周期:月刊
编辑出版:体育风尚杂志社
国内刊号:CN 44-1641/G8
国际刊号:ISSN 1674-1552
邮发代号:46-265
开本:16开
语种:中文
投稿邮箱: tyfszzs@126.com
投稿邮箱:tyfszzs@126.com
刍议《诗经》之“君子”
赵秀霞 赵秀兰
摘 要:不少资料中对《诗经·伐檀》中的“君子”一词褒贬不一,笔者试图从历来古人对“君子”一词如何看待,古书中的“君子”一词有无反用,尔、彼的不同指称作用,反语辞格古代是否盛行四个方面作出解读,认为《伐檀》中“君子”应是肯定的形象,更该作正面之解。
关键词:肯定君子;反语辞格;尔彼指称
(一)
《诗经·伐檀》共三章,采用重章迭唱的方法,结尾句分别是:“彼君子兮,不素餐兮”,“彼君子兮,不素食兮”,“彼君子兮,不素飧兮”。其中“君子”一词及本句的注释,职业中学教材是这样解释的:“那些大人先生们啊,可不白吃饭啊!这是讽刺不劳而获的剥削阶级的反话。”君子,这里泛指奴隶主阶级,并不是指有德行的人。可见,我们教科书中认为“君子”乃反面人物,此句话也是一句尖锐的反语,“不稼不穑,不狩不猎”,就是“君子”的所为。此种解释不禁让人生疑,为何历来受人褒扬的“君子”在此却是抨击、讽刺的对象呢?带着这个疑惑,笔者查阅了有关资料,结果发现竟有不同的说法。
一种认为“君子”为反面人物。如我们教科书所注,余冠英在《诗经选》中亦是此种观点。
另一种认为“君子”为正面人物,是作诗者由衷赞美之人。我们从孔颖达在《十三经注疏·毛诗传疏》中对“彼君子兮,不素餐兮”这句的疏可以看出,孔颖达对“君子”是抱着肯定态度的。那么,除毛诗外,其他三家诗对此又是如何看待的呢?查阅了王先谦的《诗三家义集疏》后,可以看到,齐、鲁、韩三家诗均说:“刺在位尸禄,贤不进用,与毛不异。”也就是说,四家诗在对待“君子”这一词的态度上是一致的,是肯定的。除此之外,我们还可进一步参看王泗原在《古语文例释》(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8月版)中的观点,很明显,针对文学研究所和余冠英的观点,王泗原针锋相对地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和理由,认为“君子”为正面形象。
(二)
正面人物,反面人物,相持不下,都可谓有理有据,那么,我们对“君子”一词究竟该作何解释呢?
一、 历来古人对“君子”一词如何看待
我们先来看《孟子·尽心上》公孙丑和孟子的对话:
公孙丑曰:“《诗》曰‘不素餐兮,君子之不耕而食,何也?”孟子曰:“君子居是国也,其君用之,则安富尊荣;其子弟从之,则孝悌忠信,不素餐兮,孰大于是?”
这是对“彼君子兮,不素餐兮”的最早解读,弥足珍贵。《诗经》大抵是周初至春秋中叶五百多年间的作品,而孟子论诗去古未远,以古人之语去解古人之诗,更能反映古人作诗之意图,故而其价值不容忽视。
再看大儒董仲舒和桓宽在《春秋繁露·仁义法》《盐铁论·国病》《盐铁论·散不足》中的解读,对君子也是持肯定态度,这对我们都有借鉴意义。
二、 古书中的“君子”一词是否有反语和讽刺解读
“君子”一词,在古文籍上基本有两义,一是地位上的,即在位者、在上者,以《老子》《周易》为代表,一是品德上的,即长者、贤者,以《论语》《左传》为代表,还有些是兼而有之。在原典中,可以发现,古人使用君子一词都很慎重,略无轻忽戏谑的表示。据一些研究人员统计,“君子”一词《孟子》中82处,《论语》中107处,《诗经》中186处,在这三百多个“君子”中,几乎无学者和注本作过反语和讽刺的解读,那么是否就《伐檀》中的三个“君子”作反语解呢?这也是值得人思考的地方。
三、 尔、彼的不同指称作用
众所周知,在古代汉语中,尔是第二人称代词,可译作“你,你们,你的”。彼是指示代词中的远指代词,相当于现代汉语的“那”。方苞的《朱子詩义补正》卷三云:“治人者食于人,以贫薄之地竭力以奉尔,望相恤也;而尔不我恤,独不闻君子之不素餐乎?言彼者,讽此人之不然也。”由此可见,诗人用“尔”称指斥的对象,用“彼”称理想人物君子,尔与彼的不同,是很让人一目了然的了。而前文我们在引述了王泗原的观点时,可以看到他也明确提出尔和彼语气的截然不同。通过这点也证明了“君子”乃正面形象。
四、 反语辞格古代是否盛行
反语辞格在我们后世使用中极为普遍,它一针见血、入木三分的揭露、讽刺作用往往是其他一些修辞手法所难以达到的。鲁迅先生对反语的运用即是信手拈来、游刃有余,他的杂文之所以被喻为匕首、投枪,文中的反语就当大放异彩。那么反语在古典中,尤其在《诗经》中是否也经常出现呢?我们发现,同样是《诗经》中的篇目,如《新台》《相鼠》《硕鼠》《君子偕老》,竟没有用反语来表达的,这不禁让人心生疑窦。究其原因:一种就是古代的人民敦厚老实,赋诗作歌多用托物起兴之手法,而对具有强烈抨击意味的反语一法并不谙熟。第二种就要从当时的社会背景来考察了,先秦时期,尽管战乱频仍,但人们的言论一般还是较为自由的,否则不会出现当时“百家争鸣”的局面,孔孟也不会周游列国,而门人食客也就不会应运而生,先秦时期的文学也就不会形成一个大观。尽管曾出现周厉王弭谤,人们道路以目的现象,但也只是少数个例。在如此自由的语言环境下,人们自然用不上反语了。
综上所述,笔者认为《诗经·伐檀》中的“君子”乃是诗人心中向往之正面人物。
参考文献:
[1]孔颖达.十三经注疏·毛诗传疏[M].
[2]王先谦.诗三家义集疏[M].
[3]王泗原.古语文例释[M].上海古籍出版社,1988.
[4]吴小如.读书丛札[M].北京大学出版社.
[5]俞志慧.《诗经·魏风·伐檀》“君子”考辨[J].中国典籍与文化,1997(3):115-118.
作者简介:赵秀霞,赵秀兰,江苏省镇江市,镇江市丹徒高级中学。